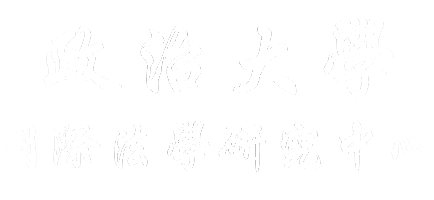張愷致:Kiobel案後美國外國侵權法案發展
張愷致*
在1980年Filartiga v. Pen-Irala案後,美國聯邦法院確立了依外國侵權法案(Alien Tort Statute,簡稱ATS)對違反「國際法(law of nations)」以及違反「美國所簽署條約」行為之事物管轄權,並在Ir re Estate of Ferdinand E. Marcos案、Kadic v. Karadzic案及Doe v. Unocal等案的發展下,將法院的管轄權擴及發生於他國領土上之「嚴重違反國際習慣法」和「強行法(jus cogen)」之行為類型。然而,隨著許多境外侵權案件在美國提起訴訟,美國法院是否應該有權將管轄權擴及於領土外之外國人及行為亦引起爭議。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2004年的Sosa v. Alvarez-Machain案中,限縮了法院依外國侵權法案得行使之管轄權範圍,在2012年的Kiobel v. Royal Dutch Petroleum案中,更嚴格限縮法院得審理之違反國際法案件類型。以下針對美國法院在外國侵權法案下依ATS案建立之涉外案件管轄權為核心,介紹歷來法院對ATS下美國法院管轄權範圍以及Kiobel案後美國實務的發展。
ATS是在1789年制訂的,此一法案原先的立法目的在於提供因違反國際法行為而受有損害之外交人員或商旅民事救濟管道,因此在當初立法理由中曾述及所欲處理案件類型包括對於外交人員之傷害以及海盜罪之處理等。在1789年制定後的兩百年間,此一法案鮮少被引用,一直到1980年的Filartiga案[註一]後,ATS才又再度登上舞台。
在Filartiga案中,聯邦上訴巡迴法院判決指出,違反刑求(Torture)者和觸犯海盜罪及販賣人口者,本質上都屬「人類之共同敵人(hostis humani generis, “an enemy of all mankind”)」,因此既ATS賦予美國聯邦法院對海盜罪的域外管轄權,考量到刑求與海盜罪同屬國際共同譴責之違反國際法行為,美國聯邦法院自亦可依ATS對於發生於美國以外之刑求案件進行管轄。在Filartiga案後,大量涉及國際法違反的民事求償在美國法院被提起,其中In re Estate of Marcos Human Rights Litig.和Kadic v. Karadzic均屬此類案件[註二]。
隨著美國聯邦法院大量對域外違反國際法之行為行使管轄權,聯邦最高法院於2004年首度在Sosa v. Alvarez-Machain案[註三]中對ATS適用下法院可建立之管轄權做出說明。在判決中,法院首先釐清ATS規範本身是一個建立法院管轄權的條款(jurisdictional clause),其本身並不是訴因(cause of action),案件之訴因仍應回歸各案中對國際法的違反;對於管轄權範圍部分,法院原則上承認ATS下可建立管轄權的違反國際法案件,並不限於十八世紀立法理由中所列舉的侵犯領事、海盜罪等類型,而可隨著當代國際法發展調整管轄權範圍,但是法院審酌管轄權範圍時,仍應留意各案件之狀況,是否與當年立法時所列舉之國際法違反類型具有相同的嚴重性。在Sosa案後,雖然聯邦最高法院以「案件違法嚴重性」限縮法院管轄權的範圍,但其並未限制美國法院對該類型案件行使域外管轄(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在2013年的Kiobel v. Royal Dutch Petroleum案,法院則嚴格的限制了ATS下聯邦法院對違反國際法侵權案件所能行使的管轄權範圍。原告Kiobel是奈及利亞人,其向美國法院控訴皇家荷蘭汽油(殼牌汽油,Shell Global)奈及利亞子公司在當地進行原油鑽探作業時,曾協助與資助(aided and abetted)奈及利亞政府鎮壓當時反對鑽探的異議人士,並導致違反國際法的情況發生,並主張皇家荷蘭汽油應該對該損害進行賠償,雖然在前審中上訴巡迴法院是以「企業法人無法負擔侵權行為」為由而駁回此案,但在上訴後,聯邦最高法院除了針對法人是否能成為侵權行為主體進行審酌外,亦對「ATS下法院的域外管轄權」問題進行探討。在論理中,聯邦最高法院首先提出「預設排除域外適用則(principle of presumption against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概念,認為為了避免國與國之間法律適用的衝突,應原則上預設美國內國法應僅適用於美國國內而不具國際適用性,縱使ATS僅為法院是否有管轄權之規範,但誠如Sosa案中法院藉由對管轄類型限縮所顯示的謹慎態度,排除域外適用的原則在ATS下仍有適用的空間,因此原則上法院對域外案件應無管轄權,縱使ATS立法歷史顯示該條文賦予聯邦法院對特定違反國際法行為管轄權,但在排除域外適用假設的適用下,除非立法者有更進一步的修法或指示,否則法院不應在立法者當初指示的違反類型外自行擴張管轄權範圍,以避免對侵擾其他國家之主權。
縱使美國在Kiobel案前擴張的管轄權政策提供了許多受害者可利用的救濟管道,但此種單一或少數國家普世性的對違反國際法行為進行管轄畢竟不是正常的現象,反而凸顯了其他國家在國際(人權)法落實上的不足。縱使Kiobel案中包括「預設排除域外適用原則」在內的許多論理都有爭執的空間,但很明顯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意抑制1980年以來大量外國違法國際法侵權案件在美國提起訴訟的現象,短期內此一修正此一政策的可能性也極低,雖然此種限縮管轄權的現象,可能使部分侵權行為受害者無法獲得適當的救濟途徑而受損害,但這個判決也讓我們反思目前國際法違反(特別是人權法)情形下,被害者在救濟途徑的選擇上究竟面對了什麼困難?又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他們放棄在本國提其訴訟救濟?在單一國家拒絕成為「國際法院」的狀況下,此些問題又應如何獲得有效的解決?
[註一] Filartiga v. Pena-Irala, 630 F.2d 876 (2d Cir. 1980).
[註二] In re Estate of Marcos Human Rights Litig., 978 F.2d 493 (1992); Kadic v. Karadzic 70 F.3d 932 (9th Cir. 2002)
[註三] Sosa v. Alvarez-Machain, 542 U.S. 692 (2004).
* 作者現就讀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LL.M.,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士,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法律碩士。聯絡方式:kcchang0317@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