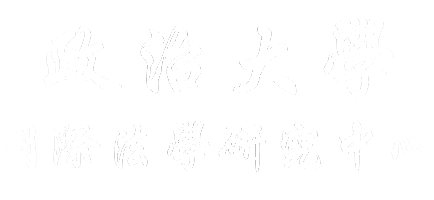譚偉恩、洪銘德:治理暖化的新途徑:裂解模式
譚偉恩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洪銘德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摘 要
為什麼目前氣候治理的全球模式會成效不彰?因為它提供的合作方法背離了主權國家的需要,沒有認真考慮暖化的問題在本質上所具有的特殊性。國際社會因為對於氣候治理普遍存在著一種迷思,相信只要有政治意願和以科學為基礎所提供的減碳目標,就足以抑制暖化,導致忽略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
本文在檢視傳統全球暖化治理機制的缺失之餘,建議一個務實可行的替代方案—裂解模式;這是一種以碳排大國為基礎的特定雙邊或有限多邊合作模式,不但可以提供發展中國家相對具體的減碳誘因,而且能促進南北國家在調適與緩解氣候變遷上的務實合作。最近美中形成的《氣候變遷共同聲明》便屬一例。
關鍵詞:裂解式途徑、氣候變遷、氣候治理、碳排放、核能
一、前言
196個《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的締約國代表在本(2014)年12月1日齊聚利馬(Lima)參與第20屆的UNFCCC締約國氣候變遷談判會議(COP20)。不過,自2009年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召開的COP15失敗以來,治理暖化問題的國際合作建制(regime)漸漸失去了信度與效率,曠時費日的冗長談判似乎最後只能提出一些口號式的書面文件,而無法促使與會的主權國家有較具體之減碳行動。此次在秘魯首都召開的COP20能克服這樣的沉痾嗎?
近幾年在UNFCCC架構下召開的COP均存在著一個問題,即談判的焦點和內容都與會員國的國家利益難以相融。這樣的情況導致全球氣候治理的努力流於空轉,相關文件中的政策淪為口號,得不到多數國家的踐行。事實上,多邊主義架構下的全球氣候治理並不是一個有效抑制暖化問題的機制,而兩起重要的國際事件隱隱透露了一些值得我們關注的訊息。
首先,在年底召開COP20以前,美中兩國利用11月在北京召開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發表聯合聲明向外界宣誓致力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1]儘管此份共同聲明的內容受到一些質疑,[2]兩大碳排國能夠在UNFCCC架構之外尋求合作且達成共識,對於提升其它國家,甚至是國際社會整體治理暖化問題的信心提升有十分正面的影響。另一起重要的國際事件是歐盟(the European Union, EU)會員國於本年10月下旬達成共識,表示將在2030年以前達成與1990年相比減排40%溫室氣體(GHGs)的目標。[3]此項由28個EU成員國同意之總體減排目標也是意義重大,因為EU尚未全然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同時西歐與東歐國家對於因應氣候變遷的立場也還有歧異。能夠在這麼不利的時空背景下堅持以EU為整體來設定減排目標,代表歐洲國家對於治理氣候變遷的談判立場沒有動搖。[4]
如上兩項國際事件反映出國際氣候談判與治理思維正在悄悄地進行轉變,並且可能最快就於利馬召開的COP20中發揮影響,或至少會在2015年巴黎(Paris)的COP21中左右「後京都機制」(post-Kyoto Mechanism)或《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的部分內容。回顧2009年以降的全球氣候談判與合作表現,以廣納南北國家為基調的全球治理模式(the model of global governance)是宣誓性大於可操作性;在此模式下的COP和由此產出的全球氣候變遷治理共識只能極為有限地處理暖化問題。相較之下,本文倡議一種量小質精的裂解模式,它聚焦在碳排大國如何參與氣候治理,並且以這些國家的自身利益作為抑制全球暖化制度設計之基礎。此外,本文針對影響暖化最重要的能源使用面向來思考具體的減碳措施,原因在於氣候治理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而各國企業(無論公營或是民間)往往才是碳排的最主要行為者。如果不能對之進行有效管理(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任何抑制暖化速率的政策都將註定失敗。而影響企業能否落實碳排相關政策的關鍵在於能源的使用;眾所皆知,傳統化石燃料(fossil fuel)是製造二氧化碳的主因,國家如果要力行減碳與抗暖,必然得從管理企業使用能源的行為著手。
論及能源使用,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於2014年11月公佈的產油不減量決議非常可能衝擊到此次COP20的談判內容,[5]因為國際原油價格將在此項決議的影響下而於相當時間內維持平穩,甚至是低廉。這對仰賴傳統化石燃料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大福音,但也可能是讓本年年底COP再度繳出不及格成績單的主要阻撓因素。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人為溫室氣體,限制它在大氣中含量的最好方法就是從能源使用面向切入,而最好的政策(理論上)就是展開能源使用的轉型。然而一旦政府實際執行能源轉型或改革之相關措施,國際與國內政治的反彈就會隨之而起,並且往往是措施的規範越嚴格,政治上的反彈力道就越大,導致過程中歧見層出不窮且在國際與國內層次擴散流轉,最終便是氣候談判與治理出現難以化解之僵局。[6]
能源的取得與使用深深影響一國經濟的發展,其中核能(nuclear energy)的使用是最複雜的議題之一。相較於其它類型的能源,核能在使用安全上的疑慮讓多數人民直覺上傾向拒絕。然而,核能在本質上具有兩面性,即它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能源需求支柱(如果該國決定減少對傳統化石燃料的使用),但核廢料的安置與核電設施的安全運轉經常造成政府與人民關係的對立。這樣的特性導致政府在制訂能源使用政策時易於陷了兩難。不過,若把核能與氣候變遷的治理併合討論時,使用核能的正當性會略有增加。舉例來說,中國目前已經成為全球碳排量最高的國家,如果國際社會想要在氣候治理上有所成效,就不可能讓中國逸脫於治理機制之外。可是我們也都知道中國在短期內是沒有意願與足夠能力去削減二氧化碳和其它加速暖化的溫室氣體,因為這麼做會妨礙其經濟成長。[7]要突破這樣的僵局便必須仰賴核能,一方面繼續穩定供應中國發展經濟過程中所需的能源消費,一方面不會因為能源的大量消費而同時製造過多的二氧化碳。
事實上,美中兩大碳排國都在利用核能因應氣候變遷(但策略不盡相同),雙方也在最近的APEC峰會上擬定相互合作的政策性聲明來削減自己的碳排量。北京方面,早已積極增加使用核能來平衡自己對於傳統化石燃料的依賴,[8]前述它與美方在上海APEC會議期間共同發表的氣候變遷共同聲明便是一項有助於中國落實能源轉型的具體策略。相較之下,在UNFCCC架構下的全球氣候治理模式顯得僵固與無法滿足許多主權國家的政策需求,不但抑制不了全球均溫的升高,而且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也漸漸突破了400 ppm(百萬分之400或0.04%)。[9]更糟的是,幾個主要的碳排大國,像是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已漸漸在具體行動上背離此種全球模式的氣候治理機制。例如:坎培拉(Canberra)中止了碳稅政策,全國電力產業的碳排量已明顯增加。多倫多(Toronto)直接表示放棄先前減排溫室氣體的承諾,不再依循「京都機制」。[10]而東京(Tokyo)在福島核災的壓力之下,增加了傳統能源的消費(例如:燃煤)以滿足全國的電力需求。
為什麼目前氣候治理的全球模式會成效不彰?因為它提供的合作方法背離了主權國家的需要,沒有認真考慮氣候暖化的問題在本質上異於過去的酸雨、河川污染、海洋迴遊漁類的養護或是破壞臭氧物質的管制等等的跨國問題。更直接地說,國際社會對於氣候治理普遍存在著一種迷思,認為只要有政治意願(political will)和以科學為基礎所提供的減碳目標就足以解決或管理氣候變遷。[11]不幸的是,抑制碳排得從每個國家的國內政治開始,該走的路線是「由下至上」(bottom-up)。如果個別國家無法知道自己能夠做什麼及如何在減碳過程中確保重要的國家利益,再科學或再嚴格的氣候治理建制都無法讓主權國家忠實地履行減排義務。本文在檢視傳統全球氣候治理機制的缺失之餘,建議一個務實可行的替代方案—裂解模式;即一種量小而質精的合作思維。一方面限縮參與合作機制的國家(僅針對像中美這樣的碳排大國),一方面聚焦在這些國家的特定能源使用政策。透過粗淺的個案觀察,本文認為以碳排大國為基礎的特定雙邊或有限多邊合作模式可以交出一張較具體的抗暖成績單,並且在效率上優於目前的全球治理模式。此外,個案研究的發現說明了核能的使用對於我們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十分必要,尤其是它可以提供發展中國家減碳的誘因和促進南北國家在調適與緩解氣候變遷上的合作。
二、裂解模式
當各國開始嘗試去思索如何治理氣候變遷和進行減碳時,國內與國際的反對聲浪還有外交合作上的困境往往也會接踵而來。何以如此呢?因為現行的全球氣候治理機制存在著對普世性規範的迷思;但普世性的國際環境建制,像是UNFCCC與具體化碳排義務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KP),並不是一個管理二氧化碳排放問題的好方法。具有普世性拘束力的法律規範在某些跨國問題的治理上確實扮演功不可沒的角色,但氣候變遷和暖化的成因非常複雜,並不適合直接套用傳統性的國際環境法律規範來進行治理。多數研究氣候治理議題的學者專家忽略了主權國家間的差異性(儘管他們注意到南北國家應予承擔不同的責任),低估了國內政治的影響。[12]但實際上,削減碳排量是一項民間私經濟活動多過官方政府行為的議題;詳言之,減碳成效好壞的關鍵是各國自身的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問題,[13]政府雖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絕對不會是主角。
鑑於國內政治的重要性不宜被忽略,裂解式途徑的理論建立在兩個與主權國家本身有關的變數上:利益(interest)與能力(capability)。不過,氣候治理終究無法僅憑碳排大國獨自的努力而竟其功,因此國與國間的合作還是不可或缺,所以在國際層次的部分,本文摻入權力(power)這個變數。利益、能力、權力三者因此成為裂解式氣候治理途徑的核心構成元素。以下由宏觀的體系層次到微觀的國家層次,逐一說明此三個重要元素的判定和其所扮演之功能。
「權力」的判準主要是以主權國家在全球碳排量(體系層次)的多寡來看;有權力的國家因此是實質影響全球碳排變化的行為者,它是否受到多邊或是雙邊氣候協議的拘束關係著整體國際社會治理氣候變遷的走向與成敗。值得注意的有兩者;首先,此處有關權力大小的判定不是以軍力或是經濟上的表現為主要依據,因為這樣會將一些重要的碳排國家(例如:加拿大、南韓、巴西等)排除在氣候治理的名單外,而這些國家對於抑制二氧化碳的成敗是有極為關鍵性的影響。其次,國家的碳排量不是一個單純的數學絕對值,而是透過彼此間比較而來。
「利益」這項變數可以幫助我們判斷一個國家有沒有意願(主觀面)去落實任何有關抑制碳排的政策;它的適用性不是固定的,而是依據不同國家的自身利益需求呈現一種浮動狀態。舉例來說,討論巴西的減碳策略時,無法不正視伐林(deforestation)的議題,[14]但這對於南非或是印度來說可能並非必要。需要注意的是,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本身在學術與實務上都還沒有定於一尊的定義,因此研究上要滿足實證性時會面臨一些限制。本文稍後的個案研究就比較偏向由中國的國家利益來進行理解與分析,並且這樣的觀察相當聚焦在該國的經濟發展與能源使用面向。
至於「能力」這個變數,則是純然從客觀面向來判斷一個國家有沒有足夠的能力(例如:科技水準的高低)去踐行抑制二氧化碳的各種政策目標。因此,或許實際情況是工業先進的北方已開發國家具有足夠的能力,但力行減碳的成本可能非常高,所以意願被大大削減,導致客觀上沒有任何具體作為。面對這樣的情形,本文在理論說明上採取將國家的意願與能力切割開來的立場,但進行個案觀察時會務實地將上述三個變數做一個整合性的思考。不過,在討論全球暖化時,主權國家的「權力」是最重要的變數,一個國家現在或是未來的碳排情況決定了它是否在氣候治理的議題領域被定位成有權力的大國(great emitters)。在這樣的理解下,中國與美國是目前最重要的碳排大國(可參考【圖1】),具有左右全球氣候治理結局的影響力,它們如果個別或共同認真執行減碳,絕對有助於地球平均溫度變化幅度的趨緩。相較之下,其它權力較小的國家很難具有這樣的影響力。

圖1:國家使用化石燃料的碳排放排比
資料來源: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Trends in Global CO2 Emissions: 2013 Report (Hague, 2013): 15
裂解式途徑面臨的最大質疑就是這個理論似乎過度關注碳排大國的角色,並且十分仰賴這些大國的合作來削減溫室氣體,但忽略小國未認真減排或是根本不減排所造成的負面衝擊。[15]這樣的質疑確實有其道理,吾人可以想像在氣候治理的合作關係中,那些選擇搭便車的小國可能會讓碳排大國的國際競爭力(經濟的或非經濟的)相對弱化。此種從主權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某種相對能力的差距所進行的推論(reasoning)反映出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甚至是相當程度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思考,其特色是邊緣化主權國家在國內層次中的兩個重要變數:利益與能力。本文並不否認碳排小國在氣候治理中的重要性,但依據學者David Vigor的見解,碳排大國會不會認真履行減碳的規範義務或政治承諾取決於它們本身的利益與能力,而不是碳排小國是否認真參與氣候治理的建制。這並非意謂著小國的搭便車行為對於國際合作毫無負面影響,而是再次強調這些國家不是左右碳排大國是否踐行削減二氧化碳的關鍵變數。[16]
氣候治理是一個必然要透過國際合作的議題,但主權國家(特別是經濟正在發展的國家)手上的利益清單中不是只有抑制暖化和削減溫室氣體這些任務,而是同時存在著好幾項不同的目標。因此在政策執行的優先順序上,環境安全的考量不見得會成為率先與認真執行之國家目標,除非減碳能同時為主權國家帶來相當程度的好處。面對這樣的情況,現行UNFCCC與KP架構下的氣候治理思維是設法提供誘因來鼓勵主權國家積極減碳,KP中的清潔發展機制(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便是一例,只不過是個為德不卒的例子。[17]本文認為,國際社會需要一個更好的制度性誘因來推動主權國家進行減碳,能源消費模式的轉變將是一個務實的選項。基本作法是提升現有的能源使用技術,讓能源使用的效率得到改善,進而漸進式改以碳排較少的再生能源或核能。[18]此一主張背後含有一個邏輯,即國際層次上對於國家碳排的管制規範越嚴格與明確(特別是減碳方案的定型化或欠缺彈性),氣候治理的目標就越難獲得實踐。相較之下,由主權國家自行單邊或相互雙邊設定能力所及且符合國家利益的減碳策略(例如:核能技術的轉移),然後在執行過程中參考彼此實際減碳的作為來增加(或減少)自己在削減溫室氣體過程中投入的資源與心力,才是一個切合實際又可行的治理途徑,儘管表面上這樣的合作模式用語模糊或義務寬鬆。
上述邏輯的核心思考就是,在各國均認可暖化問題是共同生存危機的大前提下,個別就能力所及與符合國家利益的範圍去因應氣候變遷,而不是仰賴(或迫於)全球性的強制環境法律規範去執行減碳與抗暖。其次,用「邊做邊學」(learning-by-doing)的彈性浮動方式去刺激國家效法更好或效率更佳的治理行為,帶動正向與積極的減碳實踐。[19]這樣的減碳策略不但和傳統的氣候治理思維明顯有別,還在可操作化的部分呈現較高的務實性。目前絕多數關於氣候治理的討論是聚焦在如何分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義務給KP的締約國,而不是側重個別國家如何在國內層次具體去實踐減碳目標。鑑此,本文的裂解式治理途徑建議,在尋求氣候治理的國際合作前必須先深入了解各國利益與能力的殊異。全球性的氣候治理協議倘若沒有將國家的利益與能力列入建制設計(regime design)的考量中,往往都不太能交出令人滿意的治理成績單。何以如此?首先,回顧過去近20年的氣候外交與COP,策略方向明顯偏差。UNFCCC與KP的規範是用早期環境議題的治理思維來處理一個極度複雜的氣候變遷問題。其次,充滿教條式的治理建制只是在法律上具有意義,但實踐上的貢獻微乎其微。第三,受限環境安全屬於國際公共財(public goods),全球性的氣候治理建制希望納入所有的主權國家,並將每一個國家置於法律規範的拘束之下。然而,此種合作內容中定有明確減碳目標及時間表的治理模式反而削弱了國家參與合作之意願,因為一旦加入就是在國際法上受到自己承諾之拘束,日後主權國家如果履行不了或是未完全落實義務,將可能蒙受法律上的不利益或減損國際聲譽。此種拿石頭砸腳的行為一點也不符合理性選擇的邏輯。[20]
迥異於全球模式的氣候治理,裂解式途徑採取的抗暖戰略是針對性(明確且專業)強、務實度高,以及量小質精。詳言之,成功且有效的氣候治理建制不是看它有多少國家參與,而是取決於它有沒有提供給可能參與合作的國家相當的彈性或自由度。進一步說,氣候治理應該聚焦在各國如何有效抑制自己的碳排量,而不是嘗試去談判出一個全球性的碳排上限和時間表。前面已經提及,在第一線執行減碳的主要行為者是企業而非政府,因此二氧化碳的排放情況不會是靜態的,而是相當浮動的;政府實際上很難控制碳排總量。氣候變遷的治理建制與其讓政府投入心力與資源去做定額的總量排放管制,不如用同樣的成本去設計一套獎勵研發與提升適應氣候變遷的彈性政策。此處所謂的彈性政策就是能在抗暖過程中因應情勢變遷並保持成本穩定的策略。文獻指出,科技創新是因應成本增加的最好方法,當排放二氧化碳的成本漸漸升高或是管制碳排行為的國內規範趨嚴時,企業或政府將會很快發現它們必須尋求能幫助它們降低抗暖成本的新科技。[21]不過,新科技非常倚重研發,能真正有效抑制碳排量的新科技往往在研發階段所費不貲。可以想見這不會是一般中小企業能夠負擔的經濟上開銷。另一方面,即便是財力雄厚的大企業也未必會積極的投入研發,因為研究新穎科技的結果存有很高的不確定性。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的介入就扮演非常關鍵與必要的角色;如何援助與帶動中小企業參與研究新科技,或是如何在制度面提供更多誘因或降低研發工作的風險,便是一國在國內層次上展現自我抗暖能力的具體證明。除了科技因素,減排的過程必然會出現若干「改變」,這意謂著人民需要去接納氣候變遷,並有意願在日常生活的行為上做出合宜的調適(adaptation)。在這樣一段過程中,即時性的資訊公佈與風險溝通顯得非常重要。資訊掌握度高和風險溝通得宜的國家及其人民,將較有能力預判因極端天候導致的缺水或缺糧等問題,或是可以盡早強化自己的基礎建設以因應極端天候可能帶來的生命與財產上損失。簡言之,政府可以在「研發」與「改變」兩方面扮演推手與秩序管理人的角色,這個角色一旦做成功,減排的成效就會在國內層次顯現(至少)。[22]
三、個案研究暨分析
本部分藉由中國與美國因應氣候變遷的實踐,特別中國是在核能使用方面的投資與努力來佐證先前提及的諸多「裂解式」觀點。此項粗淺的個案研究試圖回答兩個問題:(1)為什麼美中不在本年12月的COP20上討論與完成減碳事項的合作,而是提前在11月的APCE峰會上發表治理氣候變遷的共同聲明?其次,(2)為什麼中國有意願參與這樣的雙邊氣候治理模式,而不是繼續一如過往與其它經濟正在發展的碳排大國(例如:印度)站在同一陣線?
在回答上述問題之前,本文擬先說明與介紹一些關於核能與二氧化碳減排的資訊。
圖2:電力生產所致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狀況
資料來源:http://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0506/cmselect/cmenvaud/584/5111706.htm
圖3:各種能源生產方式的碳排週期比較
資料來源:http://www.nei.org/Issues-Policy/Protecting-the-Environment/Life-Cycle-Emissions-Analyses
(一)核能與碳排削減
如果國際社會想要在時間壓力下有效地抑制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各種安全威脅,[23]發展和佈署「安全的」核能供電系統將是刻不容緩之事。理論上發展和提升再生能源的使用也是一種有效抑制碳排的能源政策,但若要妥善管理或控制目前全球暖化對於地球生態的各種衝擊,恐怕實踐上不能不靠核能。[24]科學家James Hansen等人的研究指出,從1971年到2009年之間,全球核能的使用避免了至少184萬人死於因消費傳統化石能源所產生的污染。[25]核能因此在若干文獻中被列入清潔能源(clean energy),而藉助核能作為供應電子的能源使用也確實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了每年約20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26]
核能所具有的若干優點讓我們在思索如何因應氣候變遷時不能不去考慮它;首先,核能的使用可以滿足人類社會希望減少使用溫室氣體的目標,同時又對經濟發展的妨礙最小(或導致的相關成本最低),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是,核能相較於其它清潔能源,在發電的效率與穩定度上滿足人類目前絕多數經濟活動的實際需求。正因為如此,核能被視為一項緩解(mitigate)氣候變遷災難性結果的關鍵技術。表面上反核聲浪在各國此起彼落,但許多國家實際上正著手或考慮用核能來發電,以同時滿足減碳與能源安全之目標。儘管有如上的優點,但核能使用在安全層面的疑慮卻大大限縮了人民對於政府採用核能發電的接受度。事實上,是否該採用核能發電的議題已經在某些國家成為政治禁忌,因為人民無法在決定支持與反對核能使用之前用純粹理性思辯的態度去與相左立場的群體進行誠懇開放的對話。
在人類社會進入現代化生活的過程中,其實處處佈滿了風險,但我們顯然並沒有選擇拒絕現代化或是迴避所有伴隨現代化而來的風險。恰恰相反,為了取得一定之便利,我們選擇對於某些風險採取容許的心態,透過一定的科學性理解與風險評估,未逾越可容許界線的風險被現代人類社會所接受。[27]然而,在某些涉及風險的議題上,人們有時會顯得相對不夠理性;舉例來說,不少人認為航空運輸的風險高於行車或其它大眾運輸可能遭遇交通事故的風險,但科學性的統計數據一再指出,死於陸面車禍意外的罹難人數遠遠高於搭乘航空器的人數。此種人類主觀上認知的理性程度弱化並不是源自資訊的欠缺,而是肇因於對特定資訊的排斥。更確切地說,我們可能在面對某些議題時,刻意迴避平行公允地接收正反兩面的陳述。對於是否該使用核能作為替代傳統化石燃料的問題,可能就存在這樣的認知不理性與資訊接收上的偏見。[28]
水力發電也是十分可靠與便宜的能源方式,但大大受限於地理條件,因此實際上能供應的能源或滿足的需求不如核能發電。風力或太陽能是相當環保的再生能源,但能提供的電力表現並不穩定,並且技術上傳輸能源與儲存能源的問題還沒有全然克服。總體來說,除了核能外,所有目前檯面上的清潔能源都還不足以滿足人類對於電力的需求,並且在價格上也不夠友善多數的消費者。正是基於這些原因,多數的主權國家(特別是經濟正在起飛的發展中國家)無法在抑制暖化的具體作為上有較積極的表現或認真的實踐,甚至不少國家依然重度的仰賴化石燃料及傳統的火力燃煤發電。相較之下,核能的供應倘若在安全係數與技術水準上能具體提升,減少人民對此種能源使用的疑慮,那麼無論就市場潛力還是環境保護來說,它均是一個誘入與合理的選項。事實上,自從1956年第一座核能電廠開始商業運轉以來,核能發電幾度被視為是最廉價與安全的電力來源,不但在工業國家廣受歡迎,而且當時民間也沒有什麼反核聲浪。核能使用的關鍵轉捩點是在1979年,該年的美國三哩島核事故(the Three Mile Island accident)重挫了核能產業的前景。[29]雪上加霜的事件在1986年尾隨而至,前蘇聯車諾比(Chernobyl)核電廠的反應爐發生爆炸,導致爐心暴露在外,爆炸引發的火勢將輻射塵導入大氣層,隨著氣流散佈在前蘇聯西部、歐洲和若干北半球地區。根據目前的統計資料,有論者指出從1986至2004年間,全球因車諾比核災事故而死亡的人數高達98萬5000人。[30] 三哩島與車諾比的核災事故直接衝擊了人們對於核能使用的認知,並且對生產及供應核能的業者構成龐大壓力。[31] 這樣的情形也漸漸成為一種國際趨勢,越來越多的公民團體開始要求他們的政府減緩或根本廢除核能及相關的發電政策。[32]
本文不否認重大核災事變造成難以回覆的生命與財產損失,但也要同時指出這些核安事故在相當程度上誤導人們對核能風險進行正確的理解。舉個例來說,在導致人類死亡率方面,作為生活常用能源的煤碳是核能的好幾倍。[33]而這些類似的統計資料本身其實還只是保守估算,僅針對使用化石燃料產生的空氣污染對於人體健康進行評估,而沒有把使用煤炭的長期成本,例如:酸雨或是對暖化的影響列入考量。2011年的福島核災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起核能使用意外,對於這項核安意外事故的分析充滿爭議。有一種說法認為,福島事故與發生在三哩島或車諾比的核災不同,因為它是源自於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例如日本國會事故調查委員田中三彥便表示,「發生災害的基本原因是地震,如果沒有地震,絕對不會有其他問題。」[34] 換句話說,福島核災並非肇因於人禍。然而,2012年日本國會東京電力福島核電廠事故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書》(National Diet of Japan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Report)顯示全然相反的資訊,「導致意外發生的原因是人為所致,…委員會認為這起人為導致的災難與組織和制度性問題脫離不了關聯,…。」[35] 其實撇開福島核災究為人為或自然因素之爭辯,災後日本官方的統計資料已經間接傳達了一項重要訊息,那就是人類社會對於核能的誤解很深。[36] 事實上,核電廠發生意外的原因是非核能本身的人禍或天災機率非常高,其中前者更為顯著。究其根源則與貪腐、官商勾結、任人唯親(nepotism)脫離不了聯繫,[37] 而這個現象無論是在核能的輸出國還是進口國均存在。Richard Tanter的研究便顯示,個別國家的國內規範和既有的國際性核能治理機制均無法有效杜絕核能轉移時的各種貪腐現象。Tanter更進一步在其研究中證實,核能產業引起的貪腐問題是普遍存在的通例,而不是少數國家才發生之個案。[38]
總之,任何能源的使用都會有一定的社會成本或風險必須被承擔。正確理解這些成本與風險是必要的,一旦誤解便可能導致能源使用的策略錯誤,伴隨而來的就是經濟發展受挫或是環境品質受損。核能未必是因應氣候變遷唯一的能源選項,但極可能是目前檯面上最好及最理性的選項。衡平與開放式的理解核能及其風險,是治理氣候變遷不能忽略的一部分。
(二)中國與美國的氣候變遷共同聲明
2014年11月12日,中美共同發表抑制碳排的《氣候變遷共同聲明》(Joint Announcement on Climate Change)。[39]這項協議其實早在APEC會議召開前便已展開談判,內容包括中美首次明確承諾要在2030年停止碳排量的增加。中國方面,則願意將2030年設定為中國碳排的最高點,之後不再增加碳排。同時,2030年化石燃料的使用佔全中國能源比重將由目前90%降至80%。美國方面,承諾其2025年的碳排量將較以2005年為基準的碳排量下降26%到28%。這項跳脫聯合國多邊架構的氣候治理協議意義重大,因為中美兩國目前的排碳量分居全球第一與第二,大約共佔全球總排量的45%,雙方減碳協議的形成對於此時此刻在秘魯舉行的COP20還有明年在法國召開的COP21將有正面的推力。不過,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美中兩國選在以經貿事務為主的APEC會議上商討減碳的環境議題,而非選擇專責討論氣候變遷的COP20上進行相關的談判?而中國又為什麼會願意與美國形成這樣的合作?[40]
本部分嘗試用兩個面向來回答這些問題;一個是從中美雙方在談判與合作過程中的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切入,一個是從中美氣候協定的重要內容中進行分析。惟此兩面向的討論內容及觀點是相互補充而非彼此獨立或排斥。
- 中美雙方合作背後的理性選擇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小組(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主席Rajendra Pachauri認為,中國與美國於APEC達成的治理氣候變遷協議雖然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但這項協議在國際環境政治上具有激勵的效果,有助於全球各國於2015年年底達成接續KP的新規範。[41]進一步說,這項協議弱化了「京都機制」中附件一國家與非附件一國家壁壘分明的區隔,顯示中美兩大排放國有意願為達成「後京都機制」(或所謂的《巴黎協議》)共同努力。這樣的政治表態會間接對其它碳排大國(例如:印度)構成壓力,使其難以找到足夠正當的理由去繼續反對或杯葛後續的全球氣候談判或由此產生的決議。過去相當一段時間,中國在氣候治理議題上都是和發展中國家同一陣線。現在,隨著中美《氣候變遷共同聲明》的公佈,國際氣候談判場域中的競爭與合作關係將有所調整。
國內層次上,美國的國內政治一直是該國能否踐行全球性環境治理協議的重要變數,選擇在11月而不是12月與中國達合作共識,有很深的國家利益考量。在只需與中國談判或必須同時與其它國家(特別是碳排大國)共同談判的差異下,利用APEC這個平台來促成雙方關於減碳的共識,對美中都是利大於弊。從華盛頓(Washington)的角度來看,這個協議可以被視為是總統外交職權下的行政協定,不需交由國會批准,也不用承擔國際法上的義務,彈性度高且國內政治的衝擊性小,是進可攻退可守的上選。而在國際層次,此項聯合聲明可以成為美國在COP20與其它碳排大國逐一捉對廝殺的有利籌碼。更確切地說,《共同聲明》代表了美國在COP20的談判底線,如果屆時國際社會要求美國承擔較為具體的減碳責任時,美國也會要求非附件一的碳排大國(特別是像印度或巴西一類的國家)比照中國做出實質性的承諾。倘若這些國家拒絕,美國便可援引這項與中國共同治理氣候問題的文件來迫使它們讓步,或是為自己的義務不承擔進行辯護。
中國方面,雖然在內政上沒有國會政治的困境,但民間對於長期使用化石能源造成的空氣污染越來越難忍受,北京當局已經無法再坐視不管。[42]然而,一旦北京當局決定在中國展開能源使用的調整政策,必然衝擊該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速率,民間業者有可能會出現大規模的反彈,衝擊習李新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氣候變遷共同明聲》一方面引進美方的國際壓力來幫助北京當局於國內層次推動能源轉型的改革,一方面透過聲明中的具體內容向美國爭取核能相關技術的移轉或合作計畫,是個一魚兩吃的策略操作。此外,《共同聲明》的國際法拘束力相對低,因此倘若中國無法在2030年落實目前協議中的目標,也不會使自己陷入被國際社會控訴或指責的窘境,而美國也不會因此就對中國展開制裁或是透過貿易手段來施行報負。簡言之,選擇以形成《共同聲明》的方式跟美國合作可以讓中國在治理氣候變遷的議題中收穫最多,而損失最小,是一個理性選擇的上策。
除上述原因外,我們還應該關注到一項明顯的改變,那就是5年前減少碳排放的義務對於中國來說幾乎是「絕對的」經濟上不利益。但時至今日,中國內部的經濟發展已經累積到一定水準(至少在沿岸多數城市如此),經濟條件漸漸寬裕的中國民眾開始重視生活中的環境品質,例如是否有乾淨的空氣。根據若干媒體的報導,中國民眾越來越無法接受劣質的空氣品質,更反感北京當局只有在召開或主辦國際性活動時,才願意強制性的去管制鋼鐵工廠或車輛的廢氣排放。[43]在這樣的背景下,接替胡溫體制的習李新政不可能僅僅憑藉經濟發展的政績就高枕無憂,治理環境問題(特別是空氣污染)成為施政上和強化政權合法性的優先選項。中央與地方政府相繼在一定程度上展開二氧化碳減排的相關管制,例如總量和交易措施(cap-and-trade policy)的執行、獎勵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行為、補助與輔導再生能源產業,以及嚴格管制傳統重工業的廢氣或廢水排放等。有論者認為,北京當局如果要在上述環境治理事項上得到具體成效,最後不可避免的挑戰將是能源使用的轉型,即減少目前許多企業對於化石能源的依賴。[44]
資料顯示,中國至少在2007年開始就已著手進行能源使用的模式修正,在2007年所公佈的《中國應對氣候變遷國家方案》中,宣誓發展低碳能源及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核能的開發與利用。[45]為因應氣候變遷和伴隨而來的極端天候,中國逐漸在能源政策上走向低碳道路、發展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安全使用,[46]核能因此已經成為中國改善本身能源結構的必要選項之一。由於維持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大量與廉價的能源,而傳統化石能源的大規模開發與利用會對生態環境與人體健康造成嚴重衝擊,[47]積極提升核能技術及興建核能發電廠遂成為中國為自己解套的不二選項。儘管2011年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事件引起國際社會對於核安問題的再次疑慮,導致中國官方對自己現有的核能發電廠開始進行安檢,並承諾人民在確保運作無虞之前會暫停相關的設備使用或工程興建,但整體能源使用的轉型政策與既定方向並沒有改變。2012年10月下旬,國務院常務會議一口氣通過《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及《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11~2020 年),進一步明確定調核能使用在中國改善能源結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48]
事實上,中國在幾年前便已結合政府與民間之力推行新一代核能技術,而2011年11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出版的《中國因應氣候變遷之政策與行動報告》中,明確宣誓透過國家政策的引導與資金的投入,加強核能等低碳能源的開發和利用。[49]2014年9月,在《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規劃(2014-2020年)》中,再次強調在無礙安全的前提上持續發展核能,並有序推進核能發電廠的興建。[50]一言以蔽之,發展及使用核能是中國在深思熟慮後所做出的理性選擇,[51]是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治理的最佳策略。
- 《共同聲明》中的重要內容
在《共同聲明》中有幾個特別值得進一步分析的部分,它們或多或少反映了本文先前對於裂解式合作途徑的觀點及有關雙方理性選擇的分析。以下依據美國白宮官方網站所公佈的聲明內容,逐段進行討論。[52]
《共同聲明》內容的第一段提及雙方要以「建設性地的方式共同努力」(“to work constructively together”);此為一句彈性度甚高的表述,不以尋求法律拘束效果作為唯一合作方法的前提來推動彼此的建設性合作。第二段整體是本聲明的一大重點,之中有若干需要進一步解釋或探究之處;首先,以雙邊合作模式進行氣候變遷治理的重要性被華盛頓與北京「再次確認」。其次,無論是議定書、其它性質的法律文書或是具有法律效力且獲得同意的結果,應與現行適用於多國的UNFCCC系統相容。最後,中美雙方承諾要力促2015年在巴黎的COP21達成一個兼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個別國家能力與狀況的新協定。第三段(也是目前較為批評者詬病之處)放寬對合作雙方的義務要求程度,只需企圖(intend)在一定的時間範圍中達成預設的碳排目標即可。這是明確反映裂解式途徑的合作特色,即義務內容與時間表的彈性化。第四段指出,透過公開性的目標宣誓,中美雙方的合作能為全球氣候治理的談判注入新動能,鼓勵其它國家以具體的行動加入治理行列。第六段將氣候變遷的治理與經濟議題做了連結,似乎間接強調聰明的治理策略(smart action)可以驅動科技創新與經濟成長,為雙方帶來利益(例如:永續的發展、能源安全、更好的生活品質等),而不是只有成本的增加。第七段,同樣也是本協定十分關鍵的部分,強調科技創新在治理氣候變遷上的重要性,一方面可以強化國家減碳的能力,一方面肯認中美兩國對於清潔能源的投資和已經或即將展開的各種能源科技合作計畫。最後在第八段,聲明的內容明確點出核能在彼此合作關係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雖然核能不是本聲明中唯一提及的項目,但從優化能源使用的組合(optimize the energy mix)與減少碳排來看,核能顯然是一個重要的合作環節。此外,協定也提到雙方在綠色產品的貿易合作上將投注心力於清潔能源的科技轉移。
綜觀以上內容,中美《氣候變遷共同聲明》確實是一種裂解式合作途徑的具體實踐,它不只反映出兩個碳排大國在國際與國內層次上的理性計算,更凸顯中美雙方在減碳政策上的實際考量與UNFCCC架構下的全球氣候治理建制大相徑庭。
四、結論
在有關「國際合作」的諸多研究中,無論是早期的理想主義(Idealism)或是二戰後興起的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均主張透過多邊性質的國際法律規範和國際建制來促成主權國家間穩固的合作關係,以實踐彼此共同利益。不可否認,多邊主義架構下的國際合作為過去或是現在的世界秩序做出一定的貢獻,但規範或建制的存在不代表參與其中的主權國家會必然遵守踐行;[53]相反地,規範或建制中設定之義務可以在國家沒有批准條約或是沒有加入國際組織的情況下依舊得到實踐。[54]本文研究的主題—暖化的治理,就存在這樣的現象。勿寧,以廣納南北國家為基調的全球氣候治理模式無法保證主權國家的遵約(compliance),只能極為有限地處理暖化問題。相較之下,本文倡議的裂解式合作模式提供了一個較佳的治理選項,而美中兩國於本年11月在APEC峰會上攜手公佈的《氣候變遷共同聲明》佐證了此一論點。詳言之,雖然參與裂解式合作途徑的國家數目有限且規範或建制的內容設計寬鬆,但它聚焦在碳排大國國家利益的滿足,並且以這些國家自身的意願和能力作為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策略的核心思考。
跨國性的問題當然需要由主權國家「齊力」解決,因此落實合作建制中的目標該是任何國際治理機制的首要顧念。惟回顧過去20年,UNFCCC和KP在氣候變遷問題的治理成效上,顯然背離了國際合作最初的本意。表面上,COP每年召開並以聯合國名義發佈治理暖化的各種文件。實際上,地球平均溫度的增升速率和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累積一直沒有減緩過。由於國際社會對於氣候治理普遍存在著一種迷思,相信只要有政治意願(political will)和以科學為基礎所提供的減碳目標,就可以在參與國普及的基礎上有效管理氣候變遷,這顯然是忽略了國家內部政經因素的影響力。有別於傳統全球氣候治理機制的「數大變是美」思維,「量小質精」的裂解式途徑是個務實可行的替代方案;這是一種以碳排大國為基礎的特定雙邊或有限多邊合作模式,不但可以提供向來抵制減碳工作的發展中國家相對具體的減碳誘因,而且能促進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在調適與緩解氣候變遷上的務實合作。
氣候變遷的治理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議題,面對這種高難度的跨國問題,國際合作的思考宜從少而多,由下而上。此外,義務或目標的設定要盡可能貼近主權國家(特別是關鍵行為者)的利益與能力,否則治理績效必然不佳。美中雙方的《氣候變遷共同聲明》掌握了這些原則,將會是一個後續運作良好與影響層次廣泛的氣候變遷治理示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中透過科技創新、核能技術合作及綠色貿易等概念或主張,串起了彼此國家利益的交集,讓這紙治理環境議題的聲明文件因而具有極高的市場可操作性,而不是一紙只能被存放在聯合國秘書處的法律文書。
以全球為範圍和基礎展開的氣候外交及相關治理是個錯誤的合作方向,因為抑制氣候變遷不能僅靠政治意願與科學資料建構起來的國際共識,少了碳排大國的參與,或是治理建制的設計與主權國家的利益及能力無法相容時,那些國際性的協議、宣言、行動計畫、官方公報等便只會流於行式,不是無法操作就是根本無助於抗暖。方向錯誤就要修正,量小質精且聚焦於核能安全使用的裂解式合作模式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與投入更多研究的選擇。[55]
[1] David Nakamura and Steven Mufson, “China, U.S. Agree to Limit Greenhouse Gases,”Washington Post (Nov. 12), via a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conomy/china-us-agree-to-limit-greenhouse-gases/2014/11/11/9c768504-69e6-11e4-9fb4-a622dae742a2_story.html
[2] Bob Sussman, “The US-China Climate Deal: Not a Free Ride for the Chinese,” via at:http://www.brookings.edu/blogs/planetpolicy/posts/2014/11/25-us-china-climate-deal-sussman
[3] 除了削減40%的溫室氣體外,希望在2030年讓再生能源比率達到27%,而能源效率則以2007年的預測為基準改善27%。
[4] Arthur Neslen, “EU Leaders Agree to Cu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40% by 2030,”The Guardian (Oct. 24, 2014), via at: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oct/24/eu-leaders-agree-to-cut-greenhouse-gas-emissions-by-40-by-2030
[5] Jesse Solomon, “America Defiant in ‘Oil War’ with OPEC,” CNN News (Dec. 3, 2014), via at:
http://money.cnn.com/2014/12/02/investing/oil-fight-opec-us-shale-boom/;另請參考OPEC官方網頁的資料:http://www.opec.org/opec_web/en/press_room/2938.htm
[6] Thomas Hale, David Held, and Kevin Young, Girdlock: Why Global Cooperation is Failing When We Need It Mo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19-34.
[7] World Bank,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isk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via at:http://www.worldbank.org/depweb/beyond/beyondbw/begbw_14.pdf
[8] Boby Michael, Moody’s: Nuclear Energy Expands in Asia but Slows Down in Europe and US on Lower Gas Pric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Nov. 24, 2014), via at:http://www.ibtimes.co.uk/moodys-nuclear-energy-expands-asia-slows-down-europe-us-lower-gas-prices-1476238;Paul Welitzkin, China, US Diverge on Approaches to Nuclear, China Daily (USA), via at: http://usa.chinadaily.com.cn/us/2014-11/28/content_18996073.htm
[9] “Carbon Dioxide Passes Symbolic Mark,” BBC News (May 10, 2013), via at:http://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22486153
[10] 除此之外,基於國內經濟因素的考量,該國在2011年12月決定退出KP。此舉造成不少國家存疑聯合國架構下的全球氣候治理建制是否已面臨崩解。
[11] 洪德欽,「氣候變遷與歐美政策回應:專題緒論」,歐美研究,第43卷1期 (2013年3月),頁11。
[12] Mark Purdon,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tics: Moral Imperative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7 (2014): 302-303.
[13] Ibid.: 307.
[14] Daniel Nepstad, et al., “Slowing Amazon Deforestation through Public Policy and Interventions in Beef and Soy Supply Chains,” Science, Vol. 344, No. 6188 (June 2014): 1118-1123.
[15] Vitor Vasconcelos, et al., “A Bottom-up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Risky Commons,” Nature Climate Change, Vol. 3 (Jan. 2013): 797-801.
[16] David Victor, “The New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Moving beyond Gridlock on Global Warming,” via at: http://www.iwm.at/read-listen-watch/transit-online/the-new-politics-of-climate-change/
[17] 例如圖利某些特定的國家或是根本就沒有減少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參考:Institute for Energy Research, “Kyoto’s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Via at:http://instituteforenergyresearch.org/analysis/kyotos-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is-it-producing-results-for-whom/
[18] 其中核能的「安全使用」是替代傳統高碳排量化石能源的最佳方案。稍後的個案研究將會證明這個觀點。
[19] David Vigor, Global Warming Gridlock: Creating M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Protecting the Plan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3-25.
[20] David Shorr, “Climate Treaties: Why the Glacial Pace of Climate Diplomacy Isn’t Ruining the Planet,” Foreign Policy (March 17, 2014), via at: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4/03/17/think_again_climate_treaties
[21] OECD,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via at:http://www.oecd.org/env/cc/49076220.pdf
[22] 而因為裂解式合作途徑是從碳排大國著手,因此這樣的國家如果在溫室氣體的削減上做出具體成效,體系層次上必然會引起一連串有助於因應與緩解氣候變遷的改變。
[23] IPCC於本(2014)年4月公布的第五次《氣候變遷報告》(the IPCC’s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AR5)中指出,由於各國對抗全球暖化的實際行動與表訂目標仍有相當落差,推動大幅度能源使用面向的轉型刻不容緩(特別是停止使用高碳排量的化石燃料),才有可能在本世紀中期以前削減40~70%的二氧化碳和其它人為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含量,將全球平均溫度的升幅限制在攝氏2度C以下。報告精簡摘要內容可見:IPCC Working Group III,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Climate Change 2014: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 相關爭點可參考:“Is Nuclear Power Necessary for Solving Climate Change?” Via at: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2/dec/21/nuclear-power-necessary-climate-change
[25] Pushker Kharecha and James Hansen, “Prevented Mortality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Historical and Projected Nuclear Power,”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47, No. 9 (2031): 4889-4895.
[26] Mark Schrope, “Nuclear Power Prevents More Deaths Than It Causes,” via at:http://cen.acs.org/articles/91/web/2013/04/Nuclear-Power-Prevents-Deaths-Causes.html
[27] Paul Slovic, “Perception of Risk,” Science, Vol. 236, No. 4799 (April 1987):280-285.
[28] Alan Herbst and George Hopley, Energy Now: Why the Time Has Come for the World’s Most Misunderstood Energy Source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7): 1-3; 10-14.
[29] 1979年3月28日,位於美國賓州(Pennsylvania)薩士奎亞納河(Susquehanna River)的三哩島發生核電廠意外,機組部分爐心融毀(melted down),引發國際社會對核能安全的憂慮。影響所致全球近130 餘座興建中或計畫中的核電廠被取消或中止,而經歷使用核能風險的民眾也開始積極地展開反核運動。詳細的前因後果可參考(含動畫):“Backgrounder on the Three Mile Island Accident,” http://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fact-sheets/3mile-isle.html
[30] 請參考:http://www.ens-newswire.com/ens/apr2010/2010-04-26-01.html
[31] 對於全球核能產的業發展,三哩島事件是重要的轉捩點。1963至1979年之間,全球興建中的反應爐數目每年成長(除了1971和1978例外),但是三哩島事件後,1980至1998年間在美國和其它國家每年的反應爐興建數目逐年減少。此外,三哩島事件後美國就沒有再批准新的反應爐興建計畫,而之前已經核准的129件興建計畫中,只有53座反應爐最後得以完工,但是全部均未運轉。另一方面,所有核能的工程審核標準也漸漸嚴格化,施工時間往往被延長(或延宕)。
[32] 日本的福島事件就是一例,並從而強化台灣人民對於核四的反對立場。
[33] Pushker Kharecha and James Hansen, “Coal and Gas Are Far More Harmful than Nuclear Power,” via at: http://climate.nasa.gov/news/903/
[34] 「田中三彥:斷然處置 防不了核災」,自由時報(2014年2月17日)。
[35] 詳細與完整內容見:http://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3856371/naiic.go.jp/en/report/ (National Diet of Japan, November 2012).
[36] 16000多名罹難者是因為海嘯而喪失生命,真正因為反應爐輻射外洩而死亡的人數是「0」。
[37] Richard Tanter, “After Fukushima: A Survey of Corruption in the Global Nuclear Power Industry,” Asian Perspective, Vol. 37, No. 4 (Oct./Dec., 2013): 475-500.
[38] Tanter, supra note 33.
[39] U.S.-China Joint Announcement on Climate Change,全文詳見: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11/11/us-china-joint-announcement-climate-change
[40] 這個問題與國家為什麼會遵守有關環境議題的國際約定不同,它的核心考量是什麼原因左右一國加入跨國性的環境協定。以本文研究為例,可能影響國家行為的變數包括(但未必限於):環境協議的類型、落實某項環境保護義務的責任分配(建制設計)、當事方在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當事方的國內政治體制、國家在特定環境議題上的脆弱程度(the level of vulnerability)。相關研究可參考:Denise DeGarmo,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Treaties and State Behavior: Factors Influencing Coope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5): Ch. 4.
[41] 參考: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11/12/us-china-usa-climatechange-ipcc-idUSKCN0IW1MQ
[42] “Deciphering ‘APEC Blue’: Man-Made Effort or Sent from the Skies? Via at:
http://www.echinacities.com/china-media/Deciphering-APEC-Blue-Man-Made-Effort-or-Sent-from-the-Skies
[43] Edward Wong, “Outrage Grows Over Air Pollution and China’s Respons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6, 2011), via at:http://www.nytimes.com/2011/12/07/world/asia/beijing-journal-anger-grows-over-air-pollution-in-china.html?_r=0
[44] 秦天寶,「核能與可再生能源,中國大陸何去何從?」,法學新論,第38期(2012年10月),頁24-25。
[45] Danny Marks, “China’s Climate Change Policy Process: Improved but Still Weak and Fragmente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9, No.67 (2010), p.972.
[46] Gareth Thomas MP & Stewart T. Boyle, At the Energy Crossroads: Policies for a Low Carbon Economy (London: Fabian Society, 2001).
[4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能源政策(2012)白皮書》,網址: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2/Document/1233790/1233790.htm。
[48] 同上註。
[49]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因應氣候變遷之政策與行動報告》(北京: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1年),頁6。
[50] 行政院環保署,「中國大陸節能減碳之策」,網址:http://csesep.tesd.org.tw/dispPageBox/TCS/TCCP_MS.aspx?ddsPageID=CEPPNEWS1&dbid=4975328838
[5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核能安全及其高級別會議上的發言」,網址: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zcwj_611316/t863271.shtml
[52] 詳見本文註39;其中第五段的內容較龐雜且宣誓性的色彩較重,因此本文略過不特別闡明。
[53] Kal Raustiala, “Compliance and Effec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L, Vol. 32 (2000): 387-427.
[54] Beth Simmons, “Treaty Compliance and Viol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3 (2010): 274-275.
[55] Nathanael Massey and ClimateWire, “Nuclear Power Also Needed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Scientific American (April 16, 2014), via at: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nuclear-power-also-needed-to-combat-climate-change/